【來稿】私有化「思考方法學」?李天命的得與失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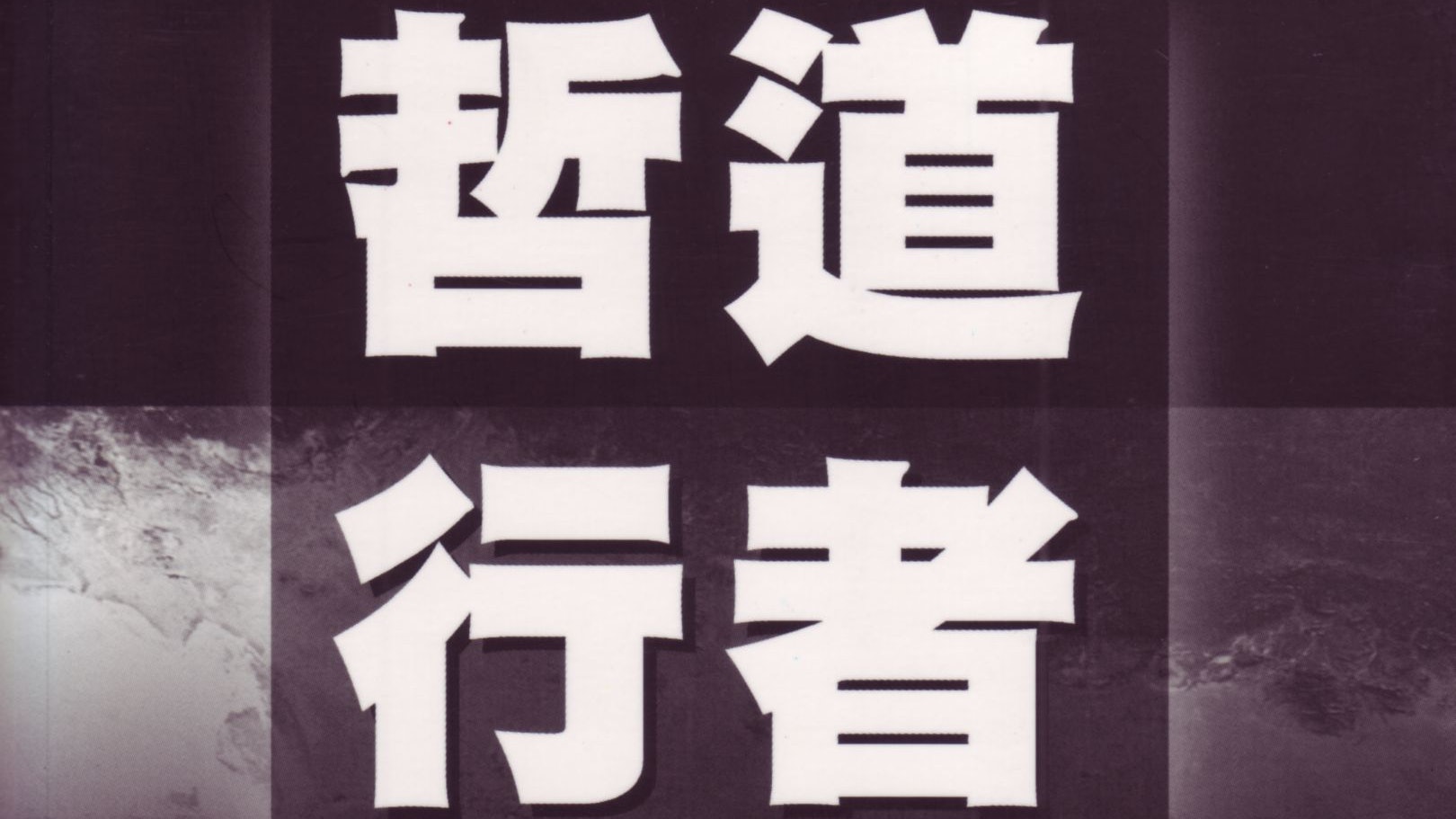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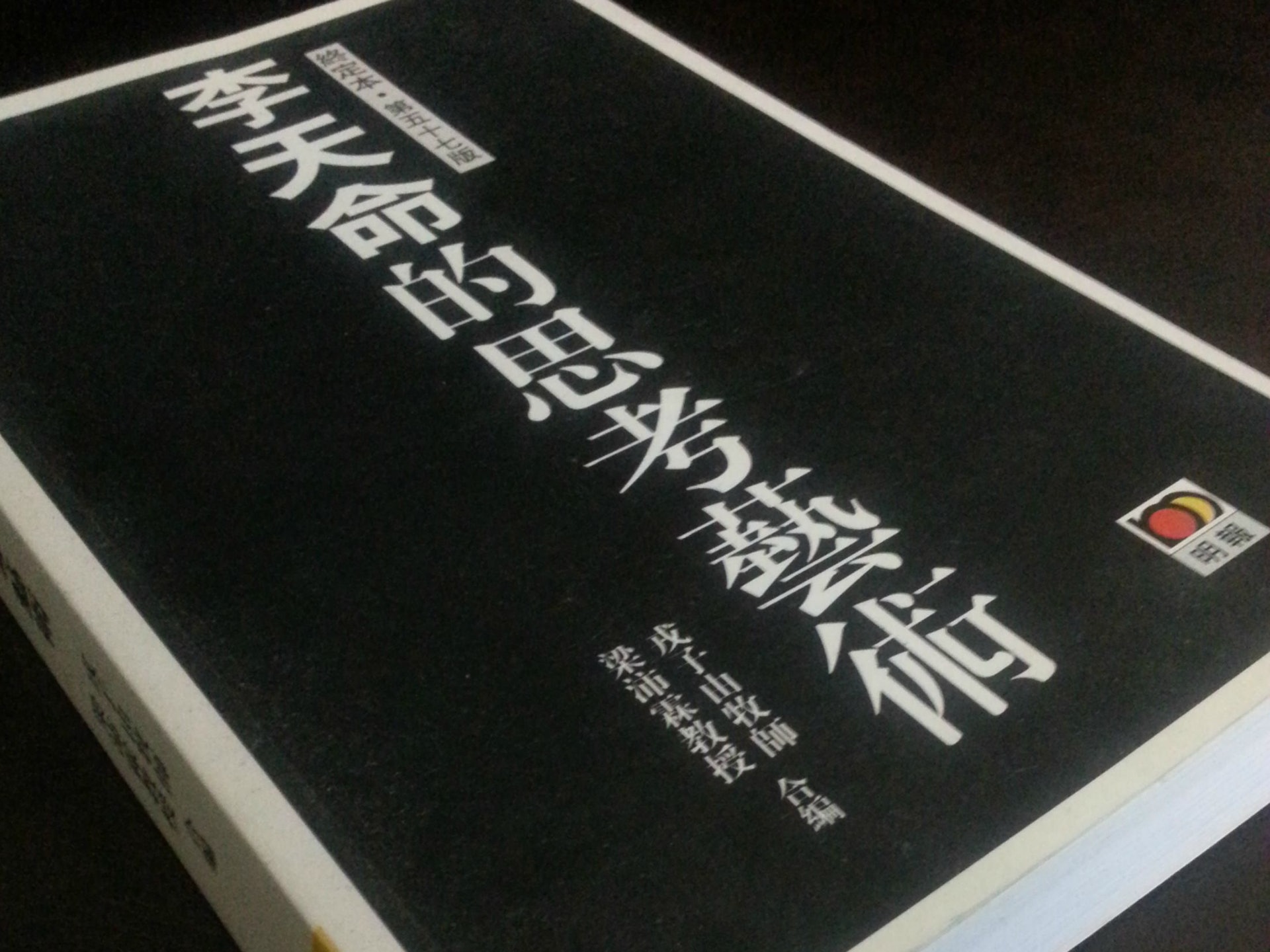
文:秦晞輝
近年歐美大為流行一門名為 critical thinking 的學問,講究 problem solving,讓讀者明白釐清目標、發問問題、尋找證據、作出推論、建立觀點等技能的重要性。Critical thinking 的書籍近年如雨後春筍,平均每年也會有十餘本相關的著作推出市面。略舉較着名的幾本如下:
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、心理學家 Daniel Kahneman 撰寫的《Thinking, Fast and Slow》(2011年)以心理學議題展開思考的《Controversy in the Psychology Classroom: Using Hot Topics to Foster critical thinking》(2012年)回應近年流行的新紀元思想的《How to Think About Weird Things: critical thinking for a New Age》第 7 版(2013年)幫助思考商業決策的《A Practical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: Deciding What to Do and Believe》第 2 版(2014年)以生物學議題展開思考的《Tools for critical thinking in Biology》(2015年)
歐美學界和社會日益提倡 critical thinking 的其中一個主因,在於資訊科技的突破。由於互聯網已為人類提供龐大資訊,人類對記憶力需求相對減少,有效組織和運用證據的分析能力,則顯得格外重要。於是,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(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)近年大力推動 critical thinking 的發展和普及,不少大專生需接受批判思考的評估測試(Critical-thinking Assessment Test),以取締側重於背誦的考試。
李天命的「思考方法學」 啟迪不少香港學生
其實本地不少哲學學者亦早具慧見,如李天命、貝剛毅、劉彥方、梁光耀等學者的著作及網站,早已將 critical thinking 介紹至香港。李天命以「思考方法學」(下文簡稱「思方學」)來推廣 critical thinking 這學問,堪為雅譯,突顯此學問重視「方法」的重點,有晚清嚴復以《群己權界論》來翻譯 John Stuart Mill 《On Liberty》的遺風。及後的學者(如貝剛毅、梁光耀等)每當講述 critical thinking 的內容時,亦直接以「思方學」稱之。
許多香港學生(包括筆者在內)是從李天命的著作開始接觸「思方學」這門學問的,從而驚嘆於思考的堂奧,對求學有重要的啟迪。然而,進大學以後,筆者便明白「思方學」並非李先生所獨創。當中大部分有關語害、邏輯、論證、謬誤的內容,在歐美 critical thinking 的教科書中早已具備。誠然,李先生對這個學門也有很多重要的創見和發展,譬如對邏輯實證論(logical positivism)原則的應用、重新界定謬誤、子矛子盾法和思考三式等。
對筆者啟迪最深的,是他在《語理分析的思考方法》對種種封閉系統、閉塞思想的批判。
我們平常會認為一些警句啟發甚深,但其實這些語句往往無所指涉、無所驗證。例如:
「歷史發展的軌跡是循必然的路走」
表面上看似蘊藏深意,但話者根本無法舉出「怎樣才算必然?」和「怎樣才算偶然?」的印證條件,於是這個語句其實只是言之無物。
將「思方學」私有化 埋沒其他哲人的心血
然而,李天命的過失,在於將「思方學」與他本人的著作畫上等號。本來以破除封閉系統為使命,卻造了一個作繭自縛的「完備系統」。
李天命在早期著作《語理分析的思考方法》中,承認「思考方法學」早已成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,他提倡的語理分析只是其中一步。然而,在其後的著作,如《哲道行者》中,他卻聲稱「思考方法學」是他所獨創,是自己從分析哲學的成果中精煉而成,無視了此前學者相近的精煉。以致因為近來一些事件,社會大眾開始認為李天命的系統顯得不合時宜時,似乎便意味着「思方學」也變得不合時宜,這是一個大謬。
歐美「思方學」其實百花盛放,內容包括各種思考方法,對批判思考有根本重要性。但是不少只從李天命作品認識「思方學」的學生,會認為「思方學」只包括語害、邏輯、論證、謬誤等元素。假設如此,Brooke Noel Moore 與 Richard Parker的「思方學」經典教科書《Critical Thinking》相當多的篇幅都不能算是「思方學」了,因為它有以下這些逾出以上元素的內容:
第一章——介紹認知偏差(cognitive bias),認知偏差屬於認知心理學的範疇第四章〈Credibility〉——介紹「可靠性」,討論「怎樣的證據具有可信性」,屬於知識論範疇第五章〈Rhetoric, the Art of Persuasion〉——介紹「修辭學」,討論說服的技巧,屬於語言學範疇
認知偏差、可靠性和修辭學明顯不屬於語理、邏輯、論證和謬誤的任何一項,那麼在李天命的追隨者眼中,難道Moore and Parker的經典教科書不能算是「思方學」?
當代哲學的發展,以及當代思考方法學的發展,已經不再局限於語理、邏輯、論證和謬誤等傳統的形式推論(formal reasoning)領域,李先生當年崇尚的邏輯實證論,今天亦早已沒落,而當年熾熱的語言學轉向(linguistic turn),今天亦不再成為分析哲學的共法。
熟習形式推論的讀者,想必早晚也會察覺到這些形式推論對於思考當代世界的社會議題,顯得十分不足。不同的思方學學者,為了促進大眾的思考能力,也不斷汲取經驗科學的素材,以完善思考方法的不足。這個轉向,正是呼應當前哲學的「自然主義轉向」(naturalistic turn)這個大趨勢,亦即我們的思考原則,需要不斷經過經驗的洗禮進行修正。
(本文為投稿,稿件可電郵至iwanttovoice@hk01.com;文章純屬作者意見,不代表香港01立場。)